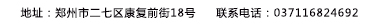|
万里难行路,“隔离”好读书——《鼠疫》与《安妮日记》阅读推荐语文组孙潇一 人们常说: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这是古人对于学识与视野并重的考量。然而今人与古人相比,虽然所读之书尚有交集,然而所行之路却大相径庭了。古人出行,正如宋元的文人画,卷轴之中是绵延不尽的山水,而人只处其中的小小一隅——清风明月,与天地合一。而今人出行,接踵摩肩的游人已将画面填满,少有留白。于是每逢旅游旺季,人们总不免要为西湖的断桥担心,唯恐“名副其实”,一语成谶。对此,我们应该追问,当下人们行路的目的,是否还像古人那样纯粹?如果人群已经遮挡了眺望的视野,那么行路除了消费、攀比、放松、疲惫与自拍究竟还剩下什么? 直至今年春季的一场疫情,所有的人都隔离在家,万里行路既然已成奢望,我们不妨冷静下来思考自己多年以来行路的盲目,圈点此时此刻读书的心得。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世界固然骄傲,但却终究有限;而阅读却可以借助巨人的肩膀,突破时空的界限,用思考来叩问灵魂。这便是读书的重要。然而比读书本身更为重要的,是读书的契机。因为读者的心境与书中的主题越契合,就越能够激发出共鸣,也就越容易有所收获。所以,对于高中阶段的同学而言,此时此刻,有两部作品似乎不能不谈——加缪的《鼠疫》与安妮的《安妮日记》。 表面看起来,这两部作品有很大的差别:作者不同——来自不同的国家,有着不同的性别,知名度也大不相同。加缪在创作《鼠疫》之前已经是知名的作家和哲学家,而写日记的安妮还是一个中学生。体裁不同——《鼠疫》是虚构的小说,是事件完整的记录;而《安妮日记》则是真实的日记,是生活零散的片段。 但是两部作品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点——均出版于年。这是二战刚刚结束的伤痛期。这意味着战争,意味着病痛,意味着反思,意味着透过它们,我们可以回顾历史,可以直面人性,可以剖析心灵,可以思考未来。而我们与《鼠疫》和《安妮日记》这两部作品最大的联结点正是当下每个人的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——“隔离”。 《鼠疫》中的隔离是工业文明与自然山水的隔离:加缪笔下的这场“鼠疫”降临在一个叫做阿赫兰的典型现代城市,这里的春天是市场上出售的春天”,这里的人们“最重要的营生是做买卖”,而且“永远是为了发财”。从这些描写中,我们可以透过加缪哲学家的视角来审视现代都市钢筋水泥、车水马龙的繁华背后掩盖的脆弱,更可以反思都市人行色匆匆、妆容精致的面孔下隐藏的悲凉。于是灵魂震动…… 在人与自然隔离之后,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接踵而至:鼠疫爆发地阿赫兰被迫封城,于是城里的人与城外的人隔离,染病的人与健康的人隔离,死去的人与幸存的人隔离——其中里厄医生与病重疗养的妻子生离死别,滞留记者雷蒙·朗贝尔与未婚妻骤然分别,自我放逐者让·塔鲁在防疫活动中不幸感染与朋友诀别…… 如果说以上这两种隔离尚可忍受的话,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的隔离则更令人感慨唏嘘。 于是,我们看到了《鼠疫》中人们对死亡的畏惧与对同类的谴责和怀疑…… 于是,我们看到了《安妮日记》里种族歧视的冰冷与战争的残酷…… 战争是野蛮的产物,但却常常成为“文明”的借口。二战期间,随着各种反犹太法令的公布,犹太人的自由被不断剥夺,最终,他们的生命也不能得到保障。于是安妮一家与她父亲的朋友达恩一家躲进了“秘密小屋”之中,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隔离生活。在隔离期间,他们两家人共同居住在狭窄的空间内。由于楼下有工人做工,为了安全起见,他们被禁止外出、打开窗帘甚至咳嗽;他们必须轻声走路、小声说话、严格作息;他们只能与人合住、互相容忍磨合、忍受物资的匮乏…… 这不是作品中虚构的隔离,这是生活中真实的隔离——从肉体到心灵。 漫长的隔离是灵魂的孤岛,于是少女安妮拿起了手中的笔,开始用记日记的方式与自己对话——她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,每天除了参与家务之外还努力学习各种知识与技能,包括多种语言、速记和数学。同时,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:除了广泛地阅读希腊罗马神话和历史作品之外,安妮还热衷于搜集王室的家谱,而如今94岁依然仪态万方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便是当年安妮
|